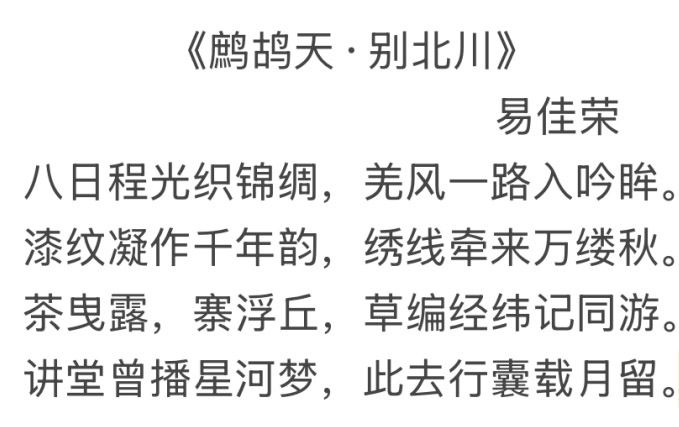七月的北川,云霧在羌山腰間流轉,像給千年文脈系了條輕柔的絲帶。作為重慶外語外事學院“羌韻北川,同心和鳴”中華文脈傳承團的一員,我踏上這片浸潤著大禹傳說與羌族智慧的土地,在水磨漆的光澤里、羌茶的醇香中、孩童的笑靨間,完成了一場關于文化傳承的青春修行。
初見水磨漆藝,是在古羌水磨漆藝傳習所那方飄著漆香的工作室里。朱紅志大師的指尖拂過漆盤上的紋樣,仿佛在與千年的羌族先民對話。“這漆藝不是冰冷的技法,是羌人對山水的熱愛,對生活的期盼。”他拿起一件繪著羊角花的漆盒,木紋與漆色交融間,我忽然讀懂了何為“匠心”——那是將民族記憶熬進漆料,讓文化基因在器物上永生。
跟著大師學做漆藝書簽時,我才明白“慢”是傳承的底色。調漆要等色漿與漆液完全融合,下筆要穩得像山澗的石頭,哪怕一筆畫歪,便要從頭再來。當我握著畫筆,看著顏料在黑色漆面上慢慢暈開,畫出一片小小的山,指尖仿佛觸到了羌族先民的溫度——他們也曾這樣,在漆器上記錄狩獵的晨光、祭祀的月色,讓文明在指尖代代相傳。朱大師說:“年輕人愿意學,這手藝就活了。”這句話像一顆種子,落在我心里,讓我忽然懂得,傳承不是復刻過去,而是用年輕的雙手,給古老技藝一個嶄新的未來。
若說水磨漆是北川的“肌理”,那羌茶便是這片土地的“血脈”。走進蓋頭山羌茶部落時,空氣中飄著苔子茶特有的清甜,基地上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:大禹門前樹,千年苔子茶。這茶不是普通的葉子,是北川的魂。我們跟著茶農學采茶,指尖掐住茶葉的嫩芽,一芽一葉。了解他們炒茶的過程:鐵鍋溫度要準,揉捻次數要夠,每一步都是祖輩傳下的“密碼”。白居易筆下“渴嘗一碗綠昌明”的詩句,此刻忽然有了實感——原來千年前的文人,也曾品過這來自北川的茶香。
最難忘的是那場公益直播。當我們架起手機,對著鏡頭介紹苔子茶的歷史、沖泡的方法時,屏幕上的點贊數不斷跳動,觀看人數慢慢漲到1622人。有網友問“怎么才能買到這樣的好茶”,有年輕人說“第一次知道羌族還有這么特別的茶文化”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直播不是簡單的“賣貨”,而是給羌茶搭了一座橋——一頭連著深山里的茶園,一頭連著外面廣闊的世界。我們傳遞的不只是茶的清香,更是鄉親們掌心的溫度,是能讓鄉村慢慢變好的,一點點微小卻堅定的力量。
支教的日子,則是這場旅程中最柔軟的篇章。在新川社區的教室里,孩子們的眼睛亮得像羌山上的星星。我們教他們應急救護知識,用繃帶模擬包扎傷口,原本害羞的小男孩會舉著手說“我學會了”;我們教他們說普通話,念繞口令“扁擔和板凳”,原本內斂的小女孩會舉著手說“我想試試”。課堂上孩子們的笑聲像羌山里的溪流,清脆又生生不息。
我還記得,在羌族文化手工課上,我正在教一個小女孩兒制作草編蜻蜓。一只小手怯生生地拉了拉我的衣角,說道:“哥哥,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樣,教別人說普通話,說我們羌族的故事。”看著她認真的模樣,我忽然懂得,支教不是“給予”,而是“相互照亮”——我們給孩子們帶去知識與視野,他們給我們帶來最純粹的熱愛與勇氣。那些天,教室里的普通話與羌族童聲相織,成了我聽過的最動人的“文脈交響”。
離開北川那天,云霧又漫上了羌山。回望這片土地,水磨漆的光澤、羌茶的醇香、孩子們的笑聲,都成了刻在我心里的記憶。這次“三下鄉”,我不是一個“旁觀者”,而是一個“參與者”——我曾用手觸摸過非遺的肌理,用聲音傳遞過文化的溫度,用真心守護過傳承的火種。朱紅志大師說,傳統文化需要年輕人“接過來,傳下去”。現在我終于明白,所謂傳承,從來不是一句口號。它是調漆時的耐心,是直播時的真誠,是教孩子念詩時的溫柔;是讓古老的技藝在年輕的指尖煥發生機,讓民族的故事在更廣闊的天地里被聽見。
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,我們或許無法像大師那樣堅守一輩子,但我們可以用自己的方式,為文脈傳承添一塊磚、加一片瓦。北川的七月已經過去,但我知道,那場關于傳承的青春答卷,才剛剛開始書寫。而我會帶著在北川收獲的感動與力量,繼續走在傳承的路上,讓更多人看見中華文脈的光芒,讓古老的智慧,在新時代的土壤里,開出更美的花。